悲愤而后有学
——《欧阳渐文选》编选者序
王雷泉
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思想界,处于万花筒般的动荡剧变中,要找出能转时代潮流而不为时俗所转的大思想家,委实不多。在长江流域,先是在下游的南京,抗战期间转移到上游的江津,存在着一个特立独行的佛教知识分子集团。他们以殉道者的精神,过着近乎苦行僧的研修生活,探讨着终极的佛教真理,却公开宣称“佛法非宗教非哲学”,与一切迷信和独断无缘。在一个义利不辨、师道不行的时代,他们高扬师道的价值,终生献身于师门事业,前赴后继,薪尽火传;然而,为了求道的真实和学术的尊严,以“依法不依人”的磊落胸怀,敢于修正师尊的思想。他们终日与青灯黄卷相伴,对数千卷佛经进行了最严格的校勘,却敢于对师尊和自己藉以入门的《楞严经》、《大乘起信论》等经典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在回到唐代唯识学这一表面看来极端保守的口号下,他们对一千余年来以天台宗、华严宗、禅宗为代表的传统中国佛学,进行了犀利的思想批判。而且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佛教的组织制度,提出“居士可以住持正法”,搅动起二千年来已成定局的僧主俗从格局。
这个佛教知识分子集团,以杨文会(1837-1911)、欧阳渐(1870-1943)、吕澂(1896-1989)三个杰出人物为代表,将中国佛学带出笼统颟顸的古代形态。在中国佛教历经劫波,即将迎接下个世纪的曙光之际,人们会再次涌动感恩的心潮,缅怀他们的世纪性贡献。杨文会,作为一个传统的佛教知识分子,最先接受西方刚创立不久的近代宗教学研究方法,创办学校,校刻佛典,被誉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父。吕澂,一个冷静求实的佛教学者,本世纪数一数二的佛学大师,与当今依然健在的台湾印顺法师同称为中国佛学双璧。而作为承上启下枢纽的欧阳渐,则是一个具有强烈宗教热忱和孤愤气质的佛教思想家和教育家,用晚年致门下陈铭枢信中语来讲,他的治学求道、讲经说法,“有激于自身而出者,有激于唐宋诸儒而出者”,他是把学问与生命体验和医民救国结合在一起的。“悲而后有学,愤而后有学,无可奈何而后有学,救亡图存而后有学。”(《内学杂著•内学序》)读欧阳之书,如同他摧金裂石的书法一样,充满着“生死事大,无常迅速”的悲凉之感,而又从字里行间激荡着不媚时俗、穷未来际的豪迈情怀。
欧阳渐在世时,他所从事的事业已是“别调孤弹”,在他死后的相当长岁月中,亦不为世俗社会和佛教界所理解,“宗教则屏为世学,世学又屏为宗教,舂粮且不能宿,盖垂青者寡矣。”(《内学杂著•与章行严书》)然而,他以“破釜沉舟,同向毗卢遮那顶上行去”的悲壮精神,带领一小批同道者,在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环境中左冲右突:他要在中国举办有如当年印度那烂陀寺一样宏大规模的佛教大学,却苦于没有多少像样的佛学教材;他要继承恩师杨仁山的遗志,对汗牛充栋的上万卷佛经进行严格的学术整理,而合格的佛学人才却寥若晨星。他别无选择,摆在面前的只能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讲学以刻经”。通过办学以培养整理佛经的人才,在整理佛经中造就佛学人才。平生所学主要体现在对佛典的选编校订及叙论中,故治学不在于一字一句的研讨,而是善于归纳,扼其大意。尤在晚年感到来日无多,故将自己的学术观点体现在讲学和书信中,以《内学杂著》和《孔学杂著》最为精要。欧阳渐晚年亲自手订二十六种著作,辑成《欧阳竟无内外学》三十册,由支那内学院蜀院于一九四三年木刻印行。这部文选主要根据于此,并酌收发表于支那内学院学报《内学》等刊物上的重要论文。全书根据文章体裁和内容分为八编,每编之内则按时代顺序排列,为方便读者阅读,选文皆由编选者重新分段标点。各编主要内容及选编理由如次:
第一编《佛学通论》,收录了《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需》、《唯识抉择谈》、《心学大意》、《〈内学〉叙言》、《辨方便与僧制》、《辨虚妄分别》、《辨二谛三性》、《辨唯识法相》等八篇文章和三篇附录。欧阳渐对佛教的系统理论,大量见于他对佛教经典的提要叙说,以及关于佛教教育的论述之中。本编所收的只是他对佛法的一般论述。面对二十年代反宗教、反迷信运动的社会大背景,以及传统佛教界衰败的现状,欧阳渐坚持佛法于宗教及哲学、科学外,别为一学,故应屏除宗教与哲学、科学的弊病:“佛法之晦,一晦于望风下拜之佛徒,有精理而不研,妄自蹈于一般迷信之臼;二晦于迷信科哲之学者,有精理而不研,妄自屏之门墙之外。”(《致章行严书》)支那内学院开学之初,欧阳渐开讲《唯识抉择谈》,列举当时中国佛学有五蔽:一、盲修禅宗者作口头禅、野狐参而废弃经教;二、思想方法笼侗而凭私见妄事创作;三、天台、贤首等宗畛域自封、得少为足,而使佛法之光日晦;四、学人于经典著述不知简择最精当之唐人之书,所以义解常错;五、学人全无研究方法而妄执难易、世出世法门。针对“时俗废疾”的空疏之病,在体用、真俗等关系上,强调即用显体、即俗修真,并辨别法相、唯识实有二系。认为唯有法相、唯识之学能对治上述五蔽。本文发表之后,引起了同出杨仁山门下的太虚法师的反驳,由此带动了对中国佛教史的深入研究。欧阳渐一生的治学充满论战的特点,范围涉及对传统中国佛教的定位,对政教关系及僧俗关系的阐述,以及对汉藏佛经翻译中佛教术语的歧解等各个方面。欧阳渐的治学重点虽是《瑜伽》、《唯识》,然中年以后旁通《般若》,融贯空有,并最终以《涅槃》为归趣。
第二编《佛教教育》,收录了《支那内学院研究会开会辞》、《法相大学特科开学讲演》、《今日之佛法研究》、《谈内学研究》、《支那内学院院训释》等五种。欧阳渐的佛教教育,具有重建现代佛教教团的意义。民国元年,他曾参加过一个短暂的“中国佛教会”,因口号偏激,纲领超越于时代而告失败。在这以后,他埋首书斋,禀承杨仁山刻经须设立居士道场的遗训,先是在金陵刻经处主持研究部,然后于1922年,和学生吕澂等人创办支那内学院,建立具有真正近代意义的中国佛教教育。抗战期间迁至四川江津,仍禀“讲学以刻经”的一贯宗旨,并发文踔厉,以激励忠愤之气。四方从游者甚众,名流贤达如梁启超、黄忏华、汤用彤、梁漱溟、陈铭枢、陈独秀等,先后入室受业,恭执弟子礼。他把佛教教育的宗旨定为:第一、哀正法灭,立西域学宗旨;第二、悲众生苦,立为人学宗旨。为支那内学院立“师、悲、教、戒”四字院训,“师、悲”着重对于人群社会的责任,“教、戒”强调学佛的理论与实践。嗣后更立四信条:“为真是真非之所寄,为法事光大,为居士道场,为精神所系。”《支那内学院院训释》系统阐述了他的教育理念和治学方向,在《释师训•辟谬五》中,列举十条经证,而倡居士堪以住持正法之说。《释教训》作于蜀院时期,形成成熟的思想体系,提出“证智无戏论,佛境菩萨行”,以顿境渐行之论,期由言教史实之真,以求观行实践之真。并确立毗昙、戒律、瑜伽、唯智(般若)、涅槃五科院学。在教育的目的、对象及方法上,欧阳渐有着许多精辟的见解。他认为佛法为一切教育之极,教育首在于确立师道,“师体曰慧,所谓知见;师道曰悲,所谓为人之学,充人之量。”教育对象有平民和豪杰之分,救今天下,应以舍生取义的豪杰之教为前提。发心须立乎其大,而作圣成佛必须笃实渐进,故概括以一个“续”字:“相续增上,是为精进。难行苦行,遍一切行,不思议行,是为精进。日月以续而明,四时以续而成。涓涓之滴,续成江河。青青之茁,续成寻柯。悲悲不已,续成萨婆若。”(《释悲训》)
第三编为《佛典研究》,收录《〈瑜伽师地论〉叙》、《〈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叙》、《〈藏要〉第一辑叙》、《〈藏要〉第二辑叙》、《赠友〈藏要〉》、《支那内学院经版图书展览缘起》、《〈经论断章读〉叙》、《精刻大藏经缘起》、《〈心经〉读》等九篇。欧阳渐继杨仁山之后,走上了中国佛教有史以来第一次科学整理藏经的不归路。“释迦以至道救世,承其后者事乃在于流通。迦叶、阿难,结集流通;龙树、无著,阐发流通;罗什、玄奘,翻译流通。自宋开宝雕版于益州,至予师杨仁山先生刻藏于金陵,为刊刻流通。先生之徂西也,付嘱于予曰:‘我会上尔至,尔会上我来,刻藏之事,其继续之。’”(《支那内学院经版图书展览缘起》)二十余年中,夙夜不敢康,刻成经籍二千卷,于俱舍、瑜伽、般若、涅槃诸科要典,皆发明要义,作成叙言。自1927年起,欧阳渐即组织人力,用新的研究方法在全部藏经中选择要典,校勘文字,编辑一套精要的佛经丛书《藏要》。原计划将菩萨藏、声闻藏中之经律论、西土此方著述,抉其要分为六辑,因战争等原因,实际上只编成三辑。编辑《藏要》是为今后彻底整理全藏作准备。“藏貌虽存,藏真早丧。一丧于金沙杂聚,而鱼目篡珠;二丧于浩渺无津,而久隳简陋;三丧于义深文涩,而屏弃谁披?经律论撰,但日增加,宋元明清,从无整理。嗟乎!琼瑰虽备,弃不庄严;海藏空罗,任其溃壅。遂使既得金而反矿,久握珠而还贫。教不能行,藏不能读,药不能医,岂不冤哉!故兹之刻藏,整理为宗,以为是先务之急也。整理应分三事:一、删芜;二、严部;三、考订。”(《精刻大藏经缘起》)对于大量汗牛充栋的后世著述,提出“余付藏外,任世浮沉”的主张,虽然惊世骇俗,却发人深省。
第四编为《论佛学书》,收入《与章行严书》、《覆陈伯严书》、《覆魏斯逸书》、《答熊子真书》、《覆欧阳浚明书》、《答陈真如书》(二则)、《与李正刚书》、《覆梅撷芸书》(七则)等书信。在这些与友朋和门人的书信中,再现了欧阳渐一生治学求道的轨迹,尤以《答陈真如书》、《覆梅撷芸书》等晚年书信,为一生佛学思想之总结。早期的《与章行严书》,向当时教育总长章士钊备述支那内学院办学特点及研究成果,并以“教育不以兴国为的,而以民能充其所以为人之量为的”,视为“教育神髓”。在致门人陈铭枢(真如)的信中,对他另一个弟子熊十力(子真)背离师说的理论失误,作了入木三分的揭示:“自既未得真甘露味饫人饥虚,而徒迹袭宗门扫荡一切之陋习、宋儒鞭辟为己之僻执,遂乃孤明自许,纵横恣睢,好作一往之辞。”认为自韩愈以来至熊十力,对佛教的根本误解,就在于误认寂灭为断灭,以清谈废事为禅而恶之。因此在晚年书信中,不厌其详地论述涅槃、法身、法界等佛教的终极命题。在《再答陈真如书》中,回顾了在接踵而来的身家痛苦中,坚忍发奋而求道有成的过程。四十岁前后,因寡母去世,由陆王心学进而学佛,由此知生死由来。五十岁前后,女儿、儿子、胞姊、爱徒相继夭折,于痛彻心脾中,通宵达旦,钻研《瑜伽》、《般若》,撰成《〈瑜伽师地论〉叙》和《〈大般若经〉叙》。至六十岁,作《〈大般涅槃经〉叙》,而后知无余涅槃为佛法之唯一宗趣,确立一生学说之重心。
第五编为《儒学通论》,选录《夏声》、《孔佛》、《孔佛概论之概论》等三篇。欧阳渐于深通程朱陆王之学后研究佛学,然后以佛摄儒,阐孔、佛之同归,本内外之两明,故将一生著述编定为“内外学”。在《孔佛概论之概论》中,以寂灭寂静义、用依于体义、相应不二义、舍染取净义四点,系统阐述儒佛二家的异同。认为“孔学是菩萨分学,佛学则全部分学也。”一切哲学,都是在求安身立命、安邦定国的道体,而其间的差异,不过是求道的深浅、广狭而已,即“佛学渊而广,孔学简而晦”。就趋向人生究竟而论,孔学是菩萨分学,佛学则全部分学。孔行而无果,佛则是行即是果。然而,根据真俗、体用不二的辩证关系,儒学若无超世出世之精神,则不能排除意、必、固、我之封执;佛学若无入世治世之方便,则流入顽空守寂的小乘境界。因此,佛不碍儒,得佛法而儒道愈精深;儒不碍佛,得儒术而佛法以普被。“知孔道之为行者说生生,生生,行也,非流转于有漏,奔于习染也。知佛法之为果者说无生,无生,果也,非熏歇、烬灭、光沉、响绝之无也。淆孔于佛,坏无生义;淆佛于孔,坏生生义。”(《孔佛》)明白体用不二的原理,则儒学的发扬光大,就是救亡图存的当务之急。
第六编为《儒典研究》,收录《四书读》、《心史叙》、《论孟课》、《毛诗课》的《叙》和《中庸传》等九篇。多为自编内学院诗文课本。欧阳渐精于文学,晚年因国难而倡忠义救国之心之气,选《毛诗课》叙曰:“绸缪在作新,作新在作气,作气在观感而愤悱。”1940年作于蜀院的《中庸传》。认为孔学有系统谈之概论,止是《中庸》一书。沿憨山德清之说,以寂灭般若为自本体,以法相唯识释性天情欲,谓舍染取净即是教。性无顿渐,教有等差。离位育参赞,是个人事,亦天下大事。故中庸之道,实大乘菩萨道。值此抗战时期,尤应提倡“狂狷中庸”,认为“中国自孟子后数千年来,曾无豪杰,继文而兴,盖误于乡愿中庸也。”在《跋〈中庸传〉寄诸友》中,认为孔、佛相通,通于此册,此非积七十年之学不能说此,将《中庸传》与《心经读》同视作晚年定论之作。
第七编为《论儒学书》,选录《孔学杂著》中的《与陶闓士书》(四则)、《覆张溥泉》、《跋〈中庸传〉寄诸友》、《覆蒙文通书》等讨论儒学的书信。抗日军兴,欧阳渐猛烈抨击产生汉奸的文化心理根源“乡愿”,“世之败坏,至是极矣。观国是者,莫不归过于贪污之官吏,豪劣之士绅,苟且偷堕之社会,此固然矣。然亦知病本之由来乎?二千余年,孔子之道废,乡愿之教行。”因此,真正的孔孟之道必取狂狷,“孙中山先生革命是一条鞭,不可杂保皇党开明专制。今日抗战到底是一条鞭,不可收容主和败类。孔子谋道不谋食,孟子舍生而取义,踽踽独行,不可夹杂乡愿、两边立足之相似教。”(《与陶闓士书三》)值此抗战,为贞元交会之非常时期,应具一段超远精神,而立天下之大本。此超乎常人思议之大本,“由二千年鄙儒谤弃之寂灭来,由二千年乡愿诬蔑之中庸来。”即佛教的最高境界“寂灭”,与儒家中庸的“素隐”,具有体与用、全体与部分的关系。“寂之境界,人欲净尽,天理纯全境界也。一泓秋水,荡涤纤尘,涟漪不动,寂灭寂然:于此悟人欲净尽境界,佛家名寂静寂灭。天光云影,人物山川,悉于中现,无劳一睇:于此悟天理纯全境界,佛家名无损恼寂灭。小乘寂灭,止用寂静,大乘兼用无损恼。今谈治国,应大乘同,触处洞然寂灭全体,故曰真孔中庸还我实落。”(《覆张溥泉》)1943年2月1日的《覆蒙文通书》,是欧阳渐逝世前二月所作,可视作最后的学术遗嘱。认为欲弘扬孔学以正人心,应谈最胜极最胜三事:第一、道定于孔孟一尊;第二、学以性道文章而得其根本;第三、研学必革命。“数千余年,学之衰弊,害于荀子,若必兴孔,端在孟子。《诗》、《书》、《春秋》,统归而摄于《礼》,《荀子•礼论》无创制之意,《中庸》本诸身,徵诸人,皆制作之能。学《荀》未免为弊人,学《孟》然后为豪杰之士也。有志然后能文章,更能进于性天。《礼》须囊括宇宙,《易》则必超于六合之外;《礼》唯集中国之大成,《易》则必契般若、瑜伽之妙,而得不可思议之神。《中庸》之素隐不已与修道,语语皆与涅槃寂静相符,渐既揭之矣,而《易》之契般若、瑜伽者,留待能者可乎!”
第八编为《人物行状》。据周邦道、章斗航所撰《欧阳大师传》,吕澂尝谓:“凡佛子之具教主规模者,愿力太宏,悲心太切,其一身所践更,往往非人所堪。”欧阳渐曾有“回将极苦代娑婆”之句,意谓愿世人无复有自己之惨痛,有之,则一人代受可也。本编选入《欧阳东泅毙哀纪碑》,由此可窥欧阳渐激于自身丧子失女的惨痛经历,而有如此血泪凝结的文章。欧阳渐去世前一年,撰《杨仁山居士传》,赞扬杨仁山于佛法中有十大功德,并认为自己批判《大乘起信论》等经典,并不违背师说,因为杨仁山在《与桂伯华书》曰:“研究因明、唯识期必彻底,为学者楷模,俾不颟顸笼侗,走入外道而不自觉。”在他去世的当年,掌门弟子吕澂撰《亲教师欧阳先生事略》,进一步指出:“师之佛学,由杨老居士出。《楞严》、《起信》,伪说流毒千年,老居士料简未纯,至师始毅然屏绝。荑稗务去,真实乃存,诚所以竟老居士之志也。初,师受刻经累嘱,以如何守成问,老居士曰:毋然,尔法事千百倍于我,胡拘拘于是。故师宏法数十年,唯光大是务,最后作老居士传,乃盛赞其始愿之宏,垂模之远焉。呜呼!师亦可谓善于继述者矣。”
二十世纪末叶,有着太多的浮躁和无奈,各类横空出世的“大师”,各种五花八门的体系,匆匆来去,各领几年乃至几月的风骚。为本已喧嚣的世间,平添几多躁音。自古英雄多寂寞,从杨、欧、吕三代大师非凡的事业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那种道义相托,薪尽火传的精神。
本书大部分由舍弟王雷波先生承担电脑打字,研究生聂士全、曾奕、宋道发诸君作了部分校对工作,特此申谢!
(《悲愤而后有学—欧阳渐文选》,上海:远东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本文以《悲愤而后有学》、《〈欧阳渐文选〉举要》为题,刊于《佛教文化》1996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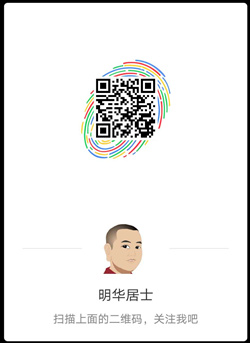
电脑上扫描,手机上长按二维码,进入明华学佛微博,点关注
温馨提示:请勿将文章分享至无关QQ群或微信群或其它无关地方,以免不信佛人士谤法!
Shou Ji Xue Fo 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