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大师对当今佛教的启迪
在纪念法显西渡斯里兰卡16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基调发言
学 诚
1600年前,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在天竺停留漫长而又短暂的八年之后(公元402~409年),孤身一人搭乘商船,经过十四天的海上航行,自东天竺到达了师子国(即今斯里兰卡)。在这里,这位老人又花了两年的光阴,抄得四部佛教梵文经书《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弥沙塞律》、《杂藏经》共一百余卷。随后,他带着之前于天竺抄得的《摩诃僧祇律》、《萨婆多律抄》、《方等般泥洹经》、《杂阿毗昙心论》、《摩诃僧祇阿毗昙》等十余部梵文经籍,万里奔波,历经惊风险浪,饱受饥渴劳苦,终于在离乡背井十四年之后,重归日夜思念的故乡。
这位不顾年事已高,毅然西行求法,宁舍生命亦无退却的老人,便是被誉为“民族脊梁”的法显大师(约公元340~426年)。大师虽然生活在距今千余年前的东晋时期,但他对当时佛教状况的准确判断、建立教法的宏深大愿、西行求法的坚勇志行及其对中国佛教产生的影响,对于我们审视当今佛教面临的问题,探寻佛教复兴的契机,亦有着莫大的启迪。下面分两个方面对此进行概要阐述。
一、补律典之阙,稳固佛教生存根本
一般认为,佛教传入汉地的时间是在公元67年。当时,两位中天竺僧人迦叶摩腾与竺法兰,在汉明帝派出的使者蔡愔迎请下来到洛阳,并翻译出第一部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到了东晋时期的后赵建武元年(公元335年),当时后赵国主石勒、石虎由于佛图澄的感化,正式允许汉人出家,这标志着佛教僧团正式为政府所认可。中国佛教僧团的合法化,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性事件。
佛法的住世与弘扬,僧团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但如果没有佛陀所制定的戒律的摄持,僧团就不可能稳定地存在,更不可能获得长久的发展。正如元照律师所说:“佛法二宝,并假僧弘。僧宝所存,非戒不立。”(《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释序文》)遗憾的是,在此之前,尽管有许多西域诸国来的僧人翻译各种各样的经典,但律典的翻译却非常罕见。直到曹魏嘉平二年(公元250年),始有天竺僧人昙摩迦罗翻译出《僧祇戒心》,汉地才开始有了戒律。但在此之后,对戒律的翻译仍显凋零。东晋道安大师因应当时佛教僧团发展的需要,根据戒律的精神及当时僧团的实际状况,制定了僧尼规范三例作为僧团应遵循的法度。尽管这三例僧尼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僧团的管理,但对于需要长期稳定发展的中国佛教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缺乏戒律的具体指导,极大地限制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随着僧团的发展与壮大,如何对其进行管理,僧人如何共住共修,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界迫在眉睫的问题。
法显大师正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显传》中记载,大师“志行明洁,仪轨整肃”,针对当时佛教经典翻译在戒律方面的缺失,他忧心忡忡,“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正是这样一种为佛教担忧的心情,促使大师发起了西行求法的誓愿。当然,这一求法愿望的萌发,也有其历史背景。自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并开辟丝绸之路以后,汉地与西域诸国的交往日益频繁。当时西域有不少国家已信奉佛教,丝绸之路的开通,为西域僧人进入汉地弘扬佛法提供了便利条件。西域僧人的前来,无形中也激发了汉地僧人对佛教发源地的神往。
种种因缘和合,大师于后秦弘始元年(公元399年),与慧景等四僧结伴,矢志西行求法,途中又遇智严等五僧,前后共十人。然而,在随后漫长而又艰辛的求法岁月中,一同结伴西行的僧人,有的半路而归,有的客死他乡,有的留居他国,最后唯有大师一人坚持走完了这条漫漫求法之路。在经历无数的磨难之后,历时十四年,大师终于满载而归,于东晋义熙八年(公元412年)从海路返回祖国,实现了西行誓愿。在返回后的第四年,即东晋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大师受到庐山慧远大师的邀请,前往扬州道场寺,与佛陀跋陀罗一起翻译大众部四十卷的《摩诃僧祇律》。
在大师出发前往西域的第二年,即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鸠摩罗什大师便来到长安,在随后十三年的时间里,罗什大师总共翻译380余卷佛经,其数量之巨,除了后来居上的玄奘大师,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无人能及。因当时佛教需求使然,罗什大师亦极重视戒律的翻译,在来长安之后的第三年,即后秦弘始六年(公元404年),便与弗若多罗开始翻译萨婆多部六十一卷本《十诵律》,并于弘始八年(公元406年)翻译完成。此外,法显大师归国前夕的弘始十五年(公元413年),北天竺僧人佛陀耶舍译出了另外一部重要律典,即昙无德部《四分律》。另外,大师归国十年后,即刘宋景平元年(公元423年),他从师子国带回的《弥沙塞律》,即弥沙塞部的《五分律》,也由佛陀什与智胜共同译出。
这样一来,短短二十年间,印度佛教上座部的五部加上大众部共六部戒律中就有四部翻译完成,极大地填补了中国佛教戒律残缺不全的状况,这也为随后南北朝时期佛教走向良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在四部律典里面,有两部都与法显大师有直接的关联,一部是《摩诃僧祇律》,一部是《弥沙塞律》。前者是大师从天竺取得,并亲自参与翻译的;后者是大师从师子国取得,由他人翻译的。在唐代以前,《摩诃僧祇律》在北方影响甚巨,《十诵律》则在江南较普及。唐代以后,因为道宣律师的著述与弘扬,《四分律》渐渐成为汉地最通行的戒律。
法显大师对于汉地佛教戒律兴盛所做出的贡献,将被后人永远铭记。这不单单是因为大师从天竺和师子国取来了两部重要的律典,并参与了其中一部的翻译,更重要的是大师那种对佛教的忧患意识、“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以及对时代需求的高度敏感性。正是这样的精神和智慧,让大师在人生花甲之年,尚能做出西行求法如此重大的决定,从而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二、纠义理之偏,开启佛法兴盛源泉
法显大师西行求得的戒律,对于僧团能够健康存活于汉地,从而使佛教在中土扎根起到了莫大的促进作用,但大师对中国佛教的贡献还不止此。大师求得并翻译的《大般涅槃经》与《杂阿毗昙心论》,对于当时佛教界义理上的偏失,亦发挥了有益的弥补作用,同时也为开启一个崭新的佛教义理时代,埋下了很好的伏笔。
汉地的佛教源自于天竺及西域诸国,因此在初始阶段受天竺及西域诸国的影响甚巨。公元一世纪,在佛教刚开始传入汉地的时候,印度大乘佛教尚未大兴,因此来自天竺的僧人如迦叶摩腾、竺法兰,以及来自安息国的僧人如安世高等,所翻译的经典多为小乘经典。但到了公元二世纪中叶之后,大乘般若空宗逐渐兴起,这在前来汉地的西域僧人所翻译的经典中便有所体现。最突出的莫过于来自月氏国的僧人支谶于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所翻译的《道行般若经》。该经中所阐发的缘起性空思想,对随后汉地佛教义学的兴起,可以说影响甚巨。被称为汉地“西行求法第一人”的朱士行,便是因《道行般若经》在翻译上存在缺憾而发愿前往西域求经的。朱士行于曹魏甘露五年(公元260年)从长安出发,经过艰苦的跋涉,终于在于阗得到《放光般若》的梵本,由他的弟子弗如檀于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送回洛阳,并在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由无叉罗和竺叔兰翻译成汉文。此《放光般若》一出,立即为学人争相研阅。此类般若经典的翻译,也为随后东晋般若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乃至形成六家七宗的鼎盛局面。到了后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随着鸠摩罗什大师入主长安译场,代表印度大乘佛教中观思想的论典,如《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被系统翻译成汉文,更是促进了汉地般若空性思想的兴盛与传播。
公元四世纪以后,随着印度佛教大乘瑜伽行派的兴起,前来汉地弘传佛法的天竺僧人越来越多地开始翻译大乘瑜伽行派的经论典籍,比如:北魏永平元年(公元508年),来自北天竺的菩提流支和中天竺的勒那摩提所翻译的世亲菩萨《十地经论》;梁武帝大同元年(公元546年),来自西天竺的真谛所翻译的无著菩萨《摄大乘论》。以这些大乘瑜伽行派的论典为依据,在汉地分别形成了地论宗和摄论宗,这也为后来汉地唯识宗的兴盛奠定了基础。与般若学兴起前期的状况类似,由于外来僧人翻译经典的解释不一,乃至有彼此矛盾之处,这种状况激起玄奘大师前往天竺求法的决心。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玄奘大师从长安出发,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抵达天竺摩揭陀国,直至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返回长安。在这长达十七年的求法之旅中,玄奘大师所求得并翻译的经典,囊括了大乘瑜伽行派主要的经论,如《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显扬圣教论》、《辨中边论》、《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等,同时也包括小乘说一切有部的主要论典,如《大毗婆娑论》、《阿毗达磨发智论》、六足论、《俱舍论》等。不仅如此,玄奘大师还把般若空宗的根本经典《大般若经》六百卷也完全翻译了过来。大师翻译的经典,其数量之巨、内容之全、译文之准确与流畅,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绝无仅有。可以说,玄奘大师翻译出来的系统而又完整的佛经论典,不但为之后汉地唯识宗的创立奠定了基础,更为汉传佛教其它各宗各派的兴盛,提供了宝贵的经典依据。
总体来看,在唐朝之前,中国佛教受天竺及西域诸国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受小乘佛教影响的阶段,主要是在东汉中后期,此时印度大乘佛教尚未大兴;第二是受印度大乘中观派影响的阶段,主要是在魏晋时期,此时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宗已经兴起;第三是受印度大乘瑜伽行派影响的阶段,主要是在南北朝及隋唐初期,此时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已经兴起。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与第三个阶段之间,也就是大约在四世纪末至五世纪初,中国佛教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从佛教僧团的组织形式上看,正由零散的组织向有序的组织过渡;从佛教义理上看,正由大乘中观派向大乘瑜伽行派过渡。而法显大师西行求法的时期,正处在这个转折的关键时期。
正如上面所说,大师所抉择的历史使命——求取并翻译律典,与当时时代对佛教的要求紧密契合,并如其所愿地为中国僧团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而在佛教义理方面,大师西行所求得并翻译的经论,如《大般涅槃经》与《杂阿毗昙心论》,也对当时的佛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对后来的佛教义理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什么大师会如此重视这两部经典呢?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此时印度佛教大乘瑜伽行派尚未兴盛,而大乘中观派的第一个兴盛时期已经过去。在当时对大乘教理的研学相对冷寂的时期,大师所翻译的这些经典有怎样的影响呢?《大般涅槃经》的翻译,直接启发了道生大师“众生皆有佛性”、“一阐提亦能成佛”等佛性论思想的提出,从而促使中国佛教从对缘起性空的哲学思辨逐渐走上了对真常唯心等心性本体论的构建。而《杂阿毗昙心论》的翻译,也使汉地学僧对毗昙学的重视又提到了日程上来。毗昙学以讲习说一切有部阿毗昙义学而得名,而《杂阿毗昙心论》则是其主要的论典之一。毗昙学的兴盛,也为汉地佛教从大乘中观派过渡到大乘瑜伽行派提供了良好的外缘。
三、总 结
回首过去,中国佛教已历经两千年的沧桑。在这沧桑历程的起步及发展阶段,来自西域、天竺乃至师子国的僧人,以及前往这些国家取经的中国僧人,都为佛教在中国的扎根及健康成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僧人在弘传佛教的同时,也担当了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友谊的使者。毫无疑问,法显大师便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作为翻译家,从经典翻译的数量上看,或许大师的成果并不突出,但对处于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国佛教来说,大师能自觉意识到当时因缘下佛教的需求和不足,并以之为己任,用高度的智慧、忘我的精神和坚韧的行动去实现和弥补,努力地推动佛教向前发展,这正是大师深为后人感佩之处。今天,中国佛教乃至世界佛教同样面临着发展的关键时期,其严峻程度与当时大师所处的历史时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佛教要想走向复兴,对僧团的有力整顿以及对佛教义理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应是必由之路。这也是法显大师西行求法的足迹带给我们的珍贵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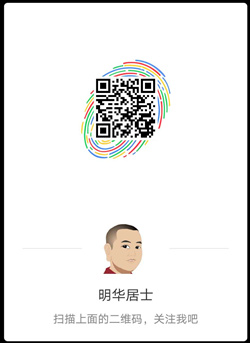
电脑上扫描,手机上长按二维码,进入明华学佛微博,点关注
温馨提示:请勿将文章分享至无关QQ群或微信群或其它无关地方,以免不信佛人士谤法!
Shou Ji Xue Fo 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