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经赞》研究序
序
方广锠
达照是1998年中国佛学院的本科毕业生。按照中国佛学院的安排,1998年秋季起跟从我学习研究生课程,专攻佛教文献学。我与达照,名为师生,实际上可说是忘年交。从达照身上,我看到解行相应的僧人风范,也看到中国佛教的希望。
本书是达照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扩充。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我给的,当时的想法,是对《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作一个异本的清理。《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属于藏外佛教文献,自形成后,一直在民间流传。宋代以后出现的多种关于《金刚经》的集解,都将它作为注解之一收入。有关情况,可以参见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或者由于这类集解的流行,《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单行本反而逐渐湮没。上个世纪20年代,日本矢吹庆辉在英国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中寻找未入藏典籍,发现其中保存着《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单行本,如获至宝,收入他的《鸣沙余韵》。其后,日本编纂出版《大正藏》时,特意在第85卷设立“古逸部”,收入敦煌等地发现的历代大藏经未收古逸典籍。《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被列为古逸部之首。由于一直在藏外流传,所以该《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有多种异本出现,而《大正藏》所收祗是其中的一种,不能反映该文献的全貌,应该重新加以整理。再说,佛教典籍在流通过程中出现异本,这属于佛教文献学应该研究的重要现象。前此,《藏外佛教文献》已经整理发表了若干种异本佛典,如《天公经》、《佛母经》、《华严十恶品经》等。我希望通过《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整理,把佛典异本演化的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此外,敦煌遗书《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被发现后,引起学者持久的兴趣,百年来研究一直在进行。已经发表的成果,既有一般的学术论文,也有学位论文。最近的成果,则有四川大学张勇先生的研究,后纳入作者的博士论文《傅大士研究》。从总体看,新的资料虽然不断被发现,但新的突破却非常有限。几十年来,研究者的结论始终局限在这部着作是后人托名之作。但到底是何人所作,什么时候所作,就所说纷纭,莫衷一是了。至于《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思想,则很少有人涉及。所以,我也希望达照的研究不要局限在所谓的“书皮之学”,即不仅要做传本、作者的考证,也要对该文献的思想倾向作一个深入的研究。
但坦率地说,达照研究后最终得到的成果之大,出于我的意外。
首先,他在敦煌遗书中发现了一批以前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新资料,从而证明早在《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出现以前,已经出现了一种名为《金刚经赞》的文献。该文献是根据无着所造《金刚般若论》科判中的“七义句”创作的,创作者应该是一个深受唯识思想影响的僧人。该文献本来以偈颂的形式单独流传,但在流传的过程中被其他人改造,从而出现诸多异本。包括加入天台思想、用无着的“十八住处”统摄全部偈颂、以及将偈颂与《金刚经》经文相配等等。其后,又出现对该《金刚经赞》的注释,并产生将“赞”改称为“颂”的倾向。最后,大约在公元822年至831年之间,有人将该《金刚经赞》改名为《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并编纂了所谓傅大士拍板唱经歌的故事。《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产生后,又经过若干演变,出现了不同的异本。达照根据目前收集到的资料,将从《金刚经赞》到《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整个演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并整理出八种互有异同的传本。这一工作,完全突破了以往研究者因把眼光仅仅集中在《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这一文本本身,从而造成的局限,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将这一文献演变发展的来龙去脉作了一个彻底的清理。
其次,在本文清理的基础上,达照对《金刚经赞》的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主张该文献以“唯识思想”为中心,涉及到唯识无境、唯识三性、五重唯识观、唯识修道五位、唯识薰习说等唯识的基本理论。同时也具有浓厚的禅法思想以及其它大乘佛教的思想。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该文献是宗派佛教兴盛时期的产物。将对《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研究提高到新的高度。
最后,作者还对文献中涉及的本生故事、典故与历史人物作了专题研究。
总之,达照在广泛掌握原始资料的前提下,在继承百年来学术界对《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书皮”与“内涵”两个方面全面地突破了前人的研究水平,其工作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就一部文献而言,考证与研究的工作能够做到这一程度,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但达照本书的意义并不局限在此。
首先,中国佛教中有些现象很值得注意。不少僧人生前名气很大,比如担任过显赫的高级僧职,死后却默默无闻,乃至现在已经完全不为人们所知。有些僧人,乃至俗人生前名气并不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名气却越来越大,甚至称祖称圣。对于前一种现象,古人就有过评论,即慧皎所谓的“寡德适时”云云。慧皎的评论一直被后世认同,以为确论。其实在我看来,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与本文无关。至于后一种现象,古代似乎没有引起人们充分的重视,现在则开始为人们所注意。傅大士就是后一种现象的代表人物之一。
傅大士,即傅翕,浙江东阳人,生活在南北朝晚期,主要活动于着名的崇佛君主梁武帝时代。由于时代风气的薰习,他成为一个崇佛的居士。作为一个下层的百姓,有着深厚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淀,却缺深研佛教义理的条件,他很自然地带有浓重的三教合一色彩,并很自然地走上信仰性佛教的道路。傅翕不甘寂寞,诣阙上书,希求得到梁武帝的赏识。但他不可能挤入以精英文化为主流的佛教上层,所以他的活动地主要在东阳一带。他的着作与事迹,也主要靠门弟子及傅氏家族而流传。从傅翕的一生,我们可以知道,三教合一思想在中国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民众基础。
从中国义理性佛教的层面来看,傅翕是一个不足道的人物。道宣的《续高僧传》对他虽有记载,乃承袭法琳《辩正论》的文字;而法琳的《辩正论》,所据乃“傅大士碑”。[①]至于隋唐诸种经录,对傅翕的着作都不屑一提。但随着经典崇拜的流行,傅翕作为转轮藏的创制者,其形象被刻造在转轮藏上,因而留名。我以为,转轮藏上的傅翕形象,可以看作义理性佛教与信仰性佛教相互连接的一个象征,因为这时在民间的信仰性佛教中,傅翕已经逐渐被塑造为弥勒的化身。这也就是《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产生的基本背景。值得注意的是,从晚唐五代起,傅翕在中国佛教禅宗中的影响逐渐加深,这与《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在这一时期的广泛流传也是互为表里的。死后几百年,傅翕总算达成生前的愿望,挤入了佛教的主流文化。但这时,傅翕已经被改造成傅大士了。
如何看待上述现象?我以为这说明中国佛教与其他一切文化形态一样,本身是可以分为若干个层次的。比如义理性佛教与信仰性佛教就是两种不同的层次。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这两种不同形态的佛教,中间并不存在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转化。《金刚经赞》,亦即《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的产生与演化过程,就是对上述观点的极好证明。从这个角度讲,“《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现象”还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其次,敦煌遗书中,佛教文献占据百分之九十以上,决定了佛教研究在敦煌学研究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与敦煌学的其他领域相比,敦煌佛教研究在我国显得相对滞后。追究其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但研究者的不谙熟佛教,或者说,佛教研究者不注意利用敦煌资料,应该是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达照有较好的佛学素养,所以,他从文本中的一个“七义句”,敏感地意识到《金刚经赞》与无着论的关系;从“一大阿僧劫”与“三大阿僧劫”差异,追索到天台思想的介入。达照的成功再次证明,研究要靠资料,而资料祗有在行家的手里才能充分显示其价值。从这一点讲,祗有佛教研究者真正重视敦煌资料,或研究敦煌佛教的研究者加强自己的佛学素养,中国的敦煌佛教研究才能真正兴盛起来。我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从中国佛学院毕业后,达照到普陀闭关,开始他修学生活的新阶段。我预祝他在解行相应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2002年3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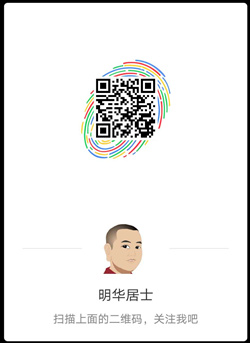
电脑上扫描,手机上长按二维码,进入明华学佛微博,点关注
温馨提示:请勿将文章分享至无关QQ群或微信群或其它无关地方,以免不信佛人士谤法!
Shou Ji Xue Fo 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