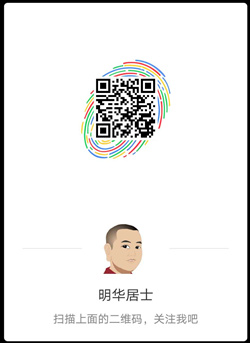
“自性”如何呈现——《六祖法宝坛经》的开示及其现代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 唐忠毛
一、见性成佛——自性及其妙用
在佛教各宗各派中,禅修是一种共法,但不同佛教宗派的禅修理论和禅修方法却有很大的不同。如,小乘修四谛十二缘起禅,大乘修六度禅,法相宗修五重唯识禅,天台有三谛三观禅,华严宗有十玄六相法界观禅……及至惠能开创的南宗禅,则立足于“自性”之上,以“无念、无相、无住”为最上乘心法,将禅从形式、方法、工具之用提升到宗门之趣。如太虚大师所言,惠能之前的教门之禅,大都实行坐禅,并根据经论和戒律来籍教悟宗,进行渐修。此教门之禅可分四个阶段——即安般禅、五门禅、念佛禅、实相禅,其心法大都主张观心住念。[1]惠能禅则革命性地抛开经论和戒律,主张直指人心,以“见性”为禅。在惠能看来,“自性”具足万法,“自性”具足妙用;故成佛作祖不假外求,只向“自性”中觅。可以说,一部《坛经》[2]皆依“自性”而立。《坛经》云:
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菩萨戒经云:我本元自性清净,若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净名经云:故知万法尽在自心,实时豁然,还得本心。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是以将此教法流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各自观心,自见本性……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若识自本性,一悟即至佛地。(《般若品第二》)
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总有,为自心迷,不见内性,外觅三身如来,不见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听说,令汝等于自身中,见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从自性生,不从外得。(《忏悔品第六》)
在惠能看来,自性具足万法,万法总在自性中。同时,此清净自性人人本自具足,只是众生心迷悟而不得识见本具的自性;只要明心见性,便能开佛知见、成就佛智、见性成佛。何为见性?《坛经》云:“但于自心常起正见,烦恼尘劳,常不能染,即是见性。”(《般若品第二》)由此可见,自性是就众生心的清净本性而言。本来众生皆有一“如来藏清净心”,只是众生由于烦恼、妄念,而使其清净心(自性)不能显现;如果众生能“于自心常起正见”,则“烦恼尘劳,常不能染,即是见性”。众生心本净,所以众生心就是佛心。在这个意义上,惠能禅便有“见性成佛”、“即心即佛”之说。而有关于心与性的关系,《坛经》这样分解道:
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 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疑问品第三》) —
在《坛经》看来,自性也就是众生心的清净本性,自心皈依自性即是自性皈依。自性不仅具足万法,也是万化的根据。追本溯源,此自性是源于流转生死,变化诸趣的如来藏性说。《起信论》谓“一心二门”,其所谓生灭门开启的就是《坛经》之烦恼、妄念的众生心,其真如门开启的即《坛经》所谓之清净自性。心、性虽别,其体是一,别处只在迷妄之间;因此,“一念觉则众生是佛,一念迷则佛是众生”。众生心本自清净,见此清净之心即是见性。若众生心起虚妄、烦恼之念,则是凡心、妄心。明心见性,就是要使本来清净无染的自性显现出来。及至神会,又在“自性”之外立“本心”、“佛心”、“无住心”等,此皆是自性的不同表达。
自性不仅本自清净、具足万法,它还具足妙用。自性显现,便能常生智慧,正如惠能谒见五祖时所说:“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离自性。”(《坛经》行由品)自性何以能常生智慧,具足妙用?那是因为自性能“内外不住,去来自由,能除执心,通达无碍”(《般若品第二》)。自性所起之念即是真如所起之念,它不同于六识于境上所起之识念,它没有任何烦恼和执着。因为,自性遍于一切法,而无念、无相、无住,不被外境所染着,这就是自性的妙用。自性显现时,心是清净的、觉悟的,无滞无碍、自由通透的状态。此种境界就是开佛知见的境界、能生智慧的境界,当然也是大解脱的境界。“明心见性”的过程可能是渐修曲折的,但真正“见性”则如拨云见日,只在刹那之顿悟,当下之立得。正如《坛经》所云:“迷来经累劫,悟则须臾间。”(《般若品第二》)
惠能《坛经》的“自性”说,归佛性于心性之中,移西方净土于刹那之间,使成佛的追求转向现实的众生自心之中。这种“内在转向”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道心性论思想的影响,但其精神实质并没有背离佛陀本怀。“自性菩提”把破除众生内心的迷妄作为成佛的标准,这使得佛教的理性光芒和现实主义品格突显出来,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内在超越”模式相互契合。
二、无念为宗——明心见性的上乘心法
惠能之前的各种佛教禅,虽有各自不同的心法,但主要以止、观为主。星云法师曾指出:“原始佛教的禅法,是以四圣谛、缘起法等作为理论基础的。在实践方面,则以蕴、界、处作为观照的内容。在次第上有四念处、八正道为修学的运用。”[3],观想法有“不净观”、“慈心观”、“因缘观”、“数息观”、“念佛观”等,这些观想之法都是针对众生自心的烦恼、妄想而进行的各种对治之方。“四念处”也叫四止念、四念住,具体包括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其中,“念”是慧观,处是境。四念处以慧观为体,由慧令念住境,从而体证涅檠。到了达摩时代的早期禅宗,其禅法较以前已经有很大改变。达摩门下的如来禅是止观的最高层次,有突破定慧二分的倾向,但其心法仍未彻底摆脱“止、观”的层面。及至惠能,他阐扬《金刚经》之“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立“无念、无相、无住”为南宗禅的根本心法。《坛经》云:
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无念;无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善知识:外离尸切相,名为无相。能离于相,即法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善知识:于诸境上,心不染,曰无念。于自念上,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绝即死,别处受生,是为大错。(《定慧品第四》)
所谓“无念”并非百物不思、一念永绝,而是“于念无念”不被外境所染着。由此可见,“无念”事实上也是立足于自性而言的,因为只有见自性之人才能真正做到“无念”,无念就是真如自性所起之念。能够“无念”自然也就“于相离相”,并“心无所住”了,此即“无念为宗”。“无念”说相对于北宗禅停止相对性分别意识念头上的“离念”,它干脆不承认心净心和念的分别,而从根本上洞察“客尘烦恼”的空之本性。“无念”就是要弃绝一切来自外部的观照和分别,而主张来自自心的本觉。所谓“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也就是根本不承认一个外在于我的“客尘世界”。从“无念”的角度来看,如果将心分为染、净,并内观与染心相别的清净心的话,那同样也就心有所住、心有所缚了。
“无念”既是对分别性、攀缘心、执着心的彻底摧毁,也是对任何来自“自我”的束缚的消解。从般若空性的角度来看,“自我”(执于我)的本质是虚妄的,“无我”才是真实的;但“无我”或者说仅仅意识到自我的虚妄性还是不够的,因为它仍然是否定性的和虚无性的,仍会引起无我与自我对立的二元论。“无念”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再次克服“无我”之念,只有当“无我”在存在上也被克服,才能悟到“真我”就是“不可得本身”。这种克服“无我”的“无念”法门,也就是《坛经》所言“不立净相”。这种层次关系,阿部正雄先生在《禅与西方思想》一书中通过青原惟信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最后依前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三种境界来说明。[4]指出第一阶段的“山是山,水是水”是一种主客二元的对立关系,正如笛卡儿所云的“自我”对外物的洞察。第二阶段“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是对第一阶段的否定,也是禅宗思想对对二元对立的“自我”的否定。但是,如果仅停留在这一阶段上,那将是虚无主义的,因为对“无我”的执着会导致一种对自我和世界漠不关心(即如《坛经》所言之百物不思的状态),从而对生活和活动没有积极的基础。第三阶段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则是进一步突破,是一中否定之否定,从而让“无我”即对自我的否定也被否定,山和水按照它们本来面目真正地肯定为山和水。[5]过程,其实就是觉悟的过程,就是撤除“自我”执着的过程,也就是“自性”呈现的过程。
三、定慧等持——明心见性的禅修特色
惠能之前的禅法,特别是小乘禅法,基本都是严格按照戒一定一慧的路径,强调由戒人定,由定发慧。达摩禅虽有突破定慧二分,以定发慧的倾向,但它终没有突破定慧相分、以定发慧的界限。及至惠能南宗禅,则彻底突破定慧相分、以定发慧的界限,定即慧、慧即定、定慧不分。由此可见,惠能的禅法已不强调外在形式的定,也不承认外在与内在、形式与本质、禅定与发慧的区别。《坛经》云:
定慧一体,不是二。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若识此义,即是定慧等学。诸学道人,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各别。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口说善语,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内外一如,定慧即等。(《定慧品第四》)
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净;悟此法门,由汝习性,用本无生,双修是正。(《机缘品第七》)
(惠能曰:)汝师戒定慧劝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劝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脱知见。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自性无非无痴无乱,念念般若观照,常离法相,自由自在,纵横尽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自性顿修,亦无渐次。(《顿渐品第八》)
在惠能看来,一切都在自性之中,真正的“戒”、“定”、“慧”都是自性的作用,在自性之中定慧是一体没有分别的。由此,惠能将外在形式的戒定打破,强调“定慧等”和“自性戒”。在此,惠能以“自性觉悟”消解了外在的“戒、定、慧”。所谓“自性戒”、“自性定”、“自性慧”,无非是说佛性本身就具戒、定、慧,它们并非存在于人的心性之外,而是为人的心性所有;所以,只要向内“明心见性”即可。
我们知道,小乘佛教的戒律是牢固建立在“业力”与“因果”之上的“有为法”,在小乘佛教的修持必须严格按照戒一定一慧的路径,以戒为首、由戒人定、由定发慧。及至大乘佛教,“业力”被“般若”取代,所以特别强调“慧观”的重要性。《起信论》倡“心体离念”,为打破由戒人定、由定发慧渐次修持的老路奠定了基础。及至南宗禅的“无念”、“定慧等”,惠能事实上已经用“无为法”的“自性戒”消解了“有为法”的戒、定、慧三学。在自性戒中,一切外在的规范性的戒律都被内化为自性的觉悟,并由此获得自由。亦如熊十先生所指出,佛教的“戒律之本,要在不违自性戒而已”,“故戒者,自性良知之自由也”。[6]诚然,戒律的外在约束是为了主体的自觉遵守而创造条件,同时,一旦形成了“自觉”的境界,也必然不违背外在的规范。也就是说广自性戒”绝不以破坏外在的规范为“合理”,更不会以离经叛道、不受戒律的行为为“合法”。不过,“自性戒”毕竟只能建立在个人的内心觉悟之上,它不能作为普遍性的规范要求。相反,对于众生来说,外在的戒律标准则是可以进行普遍化要求的规范,才是可以用来普遍推行、并作为正确修持的外在保障。将外在的规则内化为自心的觉悟这是中国化的道德传统特色,也是中国禅宗中国化之后的一大特色。在此,笔者以为,我们既要从“自性”的角度上真正领会惠能“定慧等”、“自性戒”,也要将“内在觉悟”与“外在规范”统一起来,并牢记因果、业力的作用。否则,可能会导致蔑视外在制约的、自大自狂的狂禅。
四、为道日损——明心见性的伦理向度
自性本自清净,不增不减,不垢不净,故从自性而言,并无善恶之分。正如惠能为慧明说法所云:“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坛经·行由品第一》)就佛性而言,亦无善恶之分。《坛经》云:
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阐提等,当断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无常。佛性非常非无常,是故不断,名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坛经·行由品第一》)
虽然从自性、佛性角度来说,没有善恶的相对分别;但从众生的角度而言,却有善恶之别。因此,《坛经》又处处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出发,提出明心见性的另一向度。惠能去东山求法之前先要安顿好老母,此是榜样之举。有关为善去恶的伦理向度,《坛经》中处处可见,下面这个无相颂即是集中的表达:
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
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
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
若能钻木出火淤泥定生红莲
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
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
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
——《坛经·疑问品第三》
由此可见,明心见性的过程从伦理角度来说,也是“为道日损”的过程——即不断地剔除自己不道德的行为,日复一日渐渐地让清净的自性显现出来,就像是拨云见日一样。此一过程,也如《坛经·机缘品第七》所云:“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恶,贪嗔嫉妒,谄佞我慢,侵人害物,自开众生知见。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观照自心,止恶行善,是自开佛之知见。汝须念念开佛知见,勿开众生知见。”事实上,中国禅中的伦理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深受儒家礼法思想的影响,这一点也被看成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不思善恶”与“为善去恶”是从两个不同层面来说,因此,我们应该对此有明确的区分。“不思善恶”是立于自性、佛性的真如实相层面,“为善去恶”是立于众生修养的角度而言。如果我们不从这两个层面去理解,或者将这两个层面相互混淆,那就可能导致消极的伦理结论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有些所谓“批判佛教”学者对中国佛教(特别是中国禅宗)的本觉思想进行过反思和批判,虽然其结论过于武断(批判者通过批判本觉、和的思想,进而将中国佛教、日本佛教判为“非佛教”),但其对中国佛教思想的伦理角度反思却是值得我们咀嚼的。在其伦理角度的批判中,批判者指出,由于“本觉”与“和”的思想中包含了“觉性自存”、“本来是佛”、“一切和谐”的先定预设,因此其圆融理论隐含着磨灭差异、包容善恶、调和一切的社会意识形态功能。笔者以为,在此,日本的,批判佛教者也忽视了中国佛教善恶观的应然与已然、实相与现象的两个纬度的区分。事实上,当我们从自性、佛性、实相的层面去洞察善恶的本性时,则善恶无有差别,或者说无谓善恶;但从日常现实社会来看,善恶则又朗朗分明、不容混淆。如果我们将超越的、实相层面的“无善无恶”,等同于现实层面的善恶关系,将其看作是现实社会的善恶之“已然”状态的话,就会导致不道德的伦理辩护。
五、内在超越——明心见性的超越模式
我们常将惠能开创的南宗禅视为佛教中国化最明显的代表者,这说明南宗禅在继承印度佛教传统的同时,深受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在《坛经》中,我们确实看到不少中国儒、道心性论思想,特别是儒家“性善论”的影子。而从超越模式上看,《坛经》也回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内在超越”模式之中。牟宗三先生曾指出汉语意义上的“超越”应该是一种“往而复返”。[7]郑家栋先生曾对“超越”与“内在超越”作过语义上的分析,他指出西方意义上的“超越”含有对经验界限的超越,而汉语“超越”一词基本不具有“界限”的含义。[8]我们看到,由于中国佛教既发扬了印度佛教“真俗不二”、“即人世而出世”的“中道”思想,也吸收了儒、道思想的“心性一体”、“自觉自悟”的心性模式,及至禅宗则进而归佛性于心性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心一性”的“内在超越”模式。立于“自心”、“自性”之上的超越,既是内在的、又是超越的。诚如印顺法师在《中国禅宗思想》一书中所言:
《坛经》所说的“性”,是一切法为性所化现(变化)的;而“性含万法”,“一切法在自性”,不离自性而又不就是自性的。所以性是超越心的(离一切相,性体清净),又是内在的(一切法不异于此)。从当前是一切而悟入超越的,还要不异一切,圆悟一切无非性之妙用的。这才能入能出,有体有用,理事一如,脚跟落地。在现实世界中,性是生命的主体,宇宙的本源。性显现为一切,而以心为主的。心,不只是认识的,也是行为——运动的。知觉与运动,直接地表征着性——自性、真性、佛性的作用。“见性成佛”,要向自己身心去体认,决非向色身去体悟。[9]
《坛经》反复教导说:“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不归,无所归处”。这种自心皈依自性的“内在超越”,它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强调在世俗文化或者人的自身心性之中寻求一种超越性的存在。此在《坛经》中表现也为“即人世而出世”的思想,《坛经》关于世·间与出世间以及人世与出世的关系可参下面这首偈颂: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正见名出世,邪见是世间。邪正尽打却,菩提性宛然。
——《坛经·般若品第二》
由此可见,《坛经》所谓“出世间”并非要出离此在的“世间”到别去,而是要于自心之中寻求觉悟以期明心见性——即所谓“开佛知见,即是出世”,“开众生知见,即是世间”。(《坛经·机缘晶第七》)通过“即人世而出世”,惠能将成佛的根据、方法以及可能性通通交给众生自己,指出只有自作自宰、自性自度才是最终的成佛之路。
笔者以为,在现代理性化的“祛魅”下,西方宗教的超验对象已被判为“幻想”,即尼采所谓“上帝死了”;因此,其外在超越的目标失去了根据。相反,惠能禅的“即人世而出世”,“即心即佛”的内在超越之路却彰显出了极大的理性光芒,并具有丰富的现代意义。对现代人来说,惠能禅的“自我觉悟”、“自性自度”,“见性成佛”的实践方式,有助于现代人回归“真实的自我”以及反思日渐困顿的自由观和意义世界,并为整合物质与精神提供理论启发。人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往往决定于人对于自身与世界的关系的理解之中,这种关系不是建立在冰冷的物质世界和工具思维之上,而是建立在人的超越式的理解方式上。随着工具理性的扩张,价值理性日渐边缘化,意义世界难以确立,而人在本质上又是个寻求意义的存在物,因此意义的确立是现代性的一个难题。惠能禅宗思想对意义世界的解决是非常特别的,其核心思想就是消解人们对意义的攀缘追求,回归现象和现实生活本身。本来,追求意义是人的一种本能,人总是不断地寻求现象与当下之外的意义和价值。现代理性和现代自我的最大的特点是建立在主客对立的二元之中,物质与精神、形式与实质、理想与现实、工具与价值都呈现出分离的紧张。而从行性的内在超越来看,其本质特点就在于通过回归“自性”之中将出世与人世沟通起来,将现实与理想、内在与超越、个别与普遍、暂时与永恒之间的对峙紧张一一予以消解。这种对形上学意义消解的过程,也就是对一切二元对立的紧张的消解过程,并藉此紧张的消解而获得一种“心佛合一”的真实体验。在此真实的体验中,世界的意义就当下地呈现在现象世界和日常生活里,或者说人们对意义追求的“攀缘心”已被“平常心”所取代。换句话说,在此觉悟之中人已经认识到追求意义本身就是一种虚妄,从而肯定当下的生活;于是,“日日是好日”,“砍柴担水,皆为妙道”了。这种通过消解二元对立而回归生活真实的体验,不是“返魅”,而是“觉醒”,不是“幻觉”,而是“亲证”。在惠能禅看来,当我们回归到“自性”之中的时候,现象世界就如其本来面目呈现在眼前;因此,现象世界的意义也就在其自身之中显现出来。用现代语言来表述就是,通过超越主客对立回归生命本身,回归存在本身,或者说回归人性本身,从而获得“一致性”的体验。重新获得对世界“一致性”的认同,从而处于“非反思状态”,是惠能禅用来诊疗现代意义世界和价值系统丧失的一种有效之方。事实上,“内在超越”模式也为儒、道思想所共有,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人的理想诉求方式、价值认同方式以及心理特征和审美取向。因此,探询此一“理性传统”的义理渊源,揭示此一传统的价值所依,反省此一传统的缺陷所在,完善此一传统的理论结构,都是我们应该进行研究和探讨的方向。
(下载WORD文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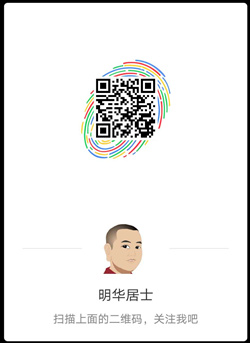
电脑上扫描,手机上长按二维码,进入明华学佛微博,点关注
Shou Ji Xue Fo Wang